
问:怎样诱惑平民使用暴力?答:给他一个合适的理由即可。
【一】
亚美尼亚大屠杀至今正好100年。虽然官方纪念日是1915年4月24日,但事实上,这起大屠杀是一个持续数年的种族灭绝行动,一直延续至1923年。有机构统计,死去的亚美尼亚人,总共达到150万。1978年,联合国将此事件定性为“种族灭绝”,与纳粹的犹太人屠杀和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并称为“20世纪三大种族屠杀”。
1915年,奥斯曼帝国气数将尽,在战争中被俄国人重创。一个叫“青年土耳其人”政党掌控大权,这个血气方刚的政权决定挽救分崩离析的国家。这种不顾一切巩固政权的初衷,就为屠杀埋下了伏笔。据材料称,1915年初,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开始逐步清除军队里的亚美尼亚人,发配他们去做苦力,当筑路工,直到劳累而死,甚至被枪杀。一些亚美尼亚人还被迫在死前自挖坟墓。
迫害加速了两者的对立。亚美尼亚人开始反抗。在凡城,亚美尼亚人赶走了土耳其人,在民族英雄阿兰姆·曼诺根的领导下,建立了亚美尼亚临时政府。一个异族的政权在土耳其东部建立起来,而且,很可能将获得俄国人的帮助。时任土耳其内政部长的塔拉特·帕夏十分惊恐,并放出狠话:“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亚美尼亚问题,就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亚美尼亚这个种族。”
青年党就开启了种族屠杀的按钮。应该说,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,需要消灭某些“内部的敌人”。缺乏治国经验的青年党人,就开始选择了最直接但又最血腥的路径处理国内矛盾。“肉体消灭一个民族”是件艰巨的工作,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,事实上也寥寥无几。但青年党真的就强硬地推进这一过程。先是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,在1915年的4月24日,600多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惨遭杀害。随后就发展到军队中的亚美尼亚士兵、政府内的亚美尼亚雇员等。在他们认为完成国家机器内部的种族清洗之后,就可以开始凡城之围。最后在凡城,开始了一场屠戮。在接下来的7年中,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人被逐个消灭。这一切都发生在不知不觉期间。
后来,亚美尼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,宣布成为一个苏维埃国家,并于1922年12月加入苏联。这才终止了奥斯曼土耳其长达7年的民族清洗和迫害。在1918年,土耳其在一战中彻底战败,青年党也被迫解散。军官出身的凯末尔开始掌握政权。土耳其也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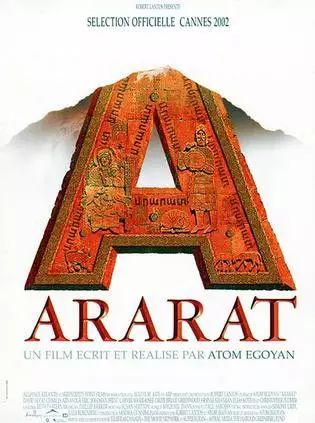
▲ 讲述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电影《Ararat》海报
【二】
总有人坚持大屠杀是“历史的偶然”。有学者指出,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缘由,在于青年党的恐惧。“大屠杀发生于政权崩溃之际,这与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有着相似的逻辑。大量犹太人于1943年之后,也就是德军在二战中处于被动局面时被送进了毒气室。”在一个政权发生动荡、失去信心的时候,就会出现这样的人道主义危机。
也有研究者表示,“谋杀性清洗典型地以一种C计划而出现,它仅在前面两种应对已洞察到的族群威胁的方案失败后才会形成。”一个共同的特点是,被屠杀的一方往往被认为将有强大的援军到来,需要尽快尽早地进行种族清洗行动。如果不杀,将会面临被杀的厄运。这种暴行在开启时,施害者是带有各种担忧、顾虑或恐惧的,因此采取“先下手为强”的手法。对现状的误判,也被认为是大屠杀的动因之一。
不过,迈克尔·曼的看法要深刻得多。在其作品《民主的阴暗面——解释种族清洗》中,系统地研究了大屠杀。这种屠杀的复杂机理,它不是一个简单的“仇恨-报复”的逻辑,而是在种种历史条件下,由世俗主义、民族主义、集体主义及恐惧心理融合而成。这不是一个道德议题,也并非“意外”,而是社会出于精致计算而自我运转的必要清洗。
这种屠杀出现在“我者”与“他者”的区分,常见于不同民族、不同宗教、不同阶级之间。往往是平和相处的不同人群,突然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“敌人”。其中一个群体获得某种正当而高尚的理由,大义凛然地处决另一个群体。死刑处决规模之大,死亡人数飙升之快,为世间之罕见,连常规战争都望尘莫及。讽刺的是,当事情结束,受害者拿着血淋淋的历史追问,但施害者也是一副痛苦之状,他们也很茫然,似乎也受了巨大的伤害。
这与齐蒙德·鲍曼的意见殊途同归。鲍曼一再强调,“大屠杀远不仅是一次失常,远不仅是人类进步坦途上的一次偏离,远不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。也就是说,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对立面,而是揭开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。”
【三】
迈克尔·曼提到一个概念,就是大屠杀的“危险区”。这个提法值得注意。
就像我们在街道上点烟,完全不会有着火的危险。但如果我们在军火库点烟,那危险就大了,随时有爆炸的可能。
历史中充斥着各种偶然事件,但若不是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紧张氛围,这些偶然事件是不可能成为社会灾难的诱因的。
在大屠杀之前,总有一种意识形态悄悄占据人们的头脑。某种正义性压倒了其人性。
怎样诱惑平民使用暴力?给他一个合适的理由即可。目前,在一些国家,依然存在小偷被愤怒的市民围殴致死的案例。只要对某个特定人群打上标签——罪犯、流氓、异教徒、劣等民族、走资派等,庸众就会从四面八法涌出,以最残暴的手段折磨他。这就是大屠杀效率惊人的奥秘,整个国家成为处决机器。他们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规模宏大的屠杀。
亚美尼亚大屠杀之前,不得不提到一个人——格卡尔普(Ziya Gokalp)。他是土耳其著名爱国诗人、理论家,赋予土耳其全新的种族主义理念——一种土耳其化而非奥斯曼化的价值体系。这就意味着,在日益瓦解的奥斯曼帝国体系中,全新的民族主义在小亚细亚再度升起。“鉴于奥斯曼传统,被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强化之后,他把民族准则看成确凿无疑地尚武的和国家主义的,这对年轻的官僚及军官有吸引力。”同时,格卡尔普还有一个论调,就是公开谴责“奥斯曼多民族特性扼杀了土耳其的民族精神”,这些话在土耳其民众中产生了剧烈的回响。虽然格卡尔普的本意只是希望土耳其的强大与繁荣,但他却无意地为清洗作了理论准备。“社会有机论”已经变成一种激进的思潮,荡漾在土耳其国内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导火索,一些亚美尼亚人被认为是叛国者。土耳其人就按下了大屠杀的按钮。
在民族主义觉醒的时刻,意味着风险的到来。迈克尔·曼认为,这是一种“社会有机论”——将少数群体排除出国家所有成员之外。衡量的依据或者是民族,或者是宗教,又或者是阶级。
社会有机论认为,社会是一个体系,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构成的紧密整体。这个体系只能从其结构运转的意义上去理解。体系要存在下去,它的需求就必须得到满足。它是所有群体压迫、群体清洗的起点。它首先在人群中划清谁是“我者”,谁是“他者”,并迅速地打上某种标签。然后,就是强化这种认同,模拟出敌我概念。只要是“他者”,哪怕是妇孺也不会放过。
在激动人心的口号中,藏着难以觉察的危险;当一个人群可以清晰地被标签之时,他们就会陷入危险之中。一个社会可以清晰地辨认“我者”与“他者”时,就有了对立的可能。无论是极权社会,还是民主社会,大屠杀的基因并没有消除。
人类依然行走在“危险区”里。种族理论、民族理论、国家理论、阶级理论等依然有着巨大的市场,伴随着资源有限论、地缘政治论等现实主义学说,人类依然对彼此充满敌意。亚美尼亚大屠杀过去了100年,可历史的真相,一直被某些人极力遮掩。至今仍有土耳其一口咬定“当时屠杀是必要的”。土耳其作家奥尔罕·帕慕克由于在小说《雪》中承认该事件,而遭到了政府的驱逐。人类之所以不敢认错,是因为当时的价值体系,今日仍在发挥作用。
新的时代,人类依然未能摆脱危险区。一个诱因,就能点燃“军火库”,就能让人类文明回到中世纪。
21世纪了,我们比一百年前进步了多少呢?


腾讯·大家专栏作者,政治学博士,昼伏夜出,读书写作。脾气正变得越来越好。

